最近出了趟远门,飞机上,无事可做,只好读书。随行所带的,是赵宗彪的新书——《史记里的中国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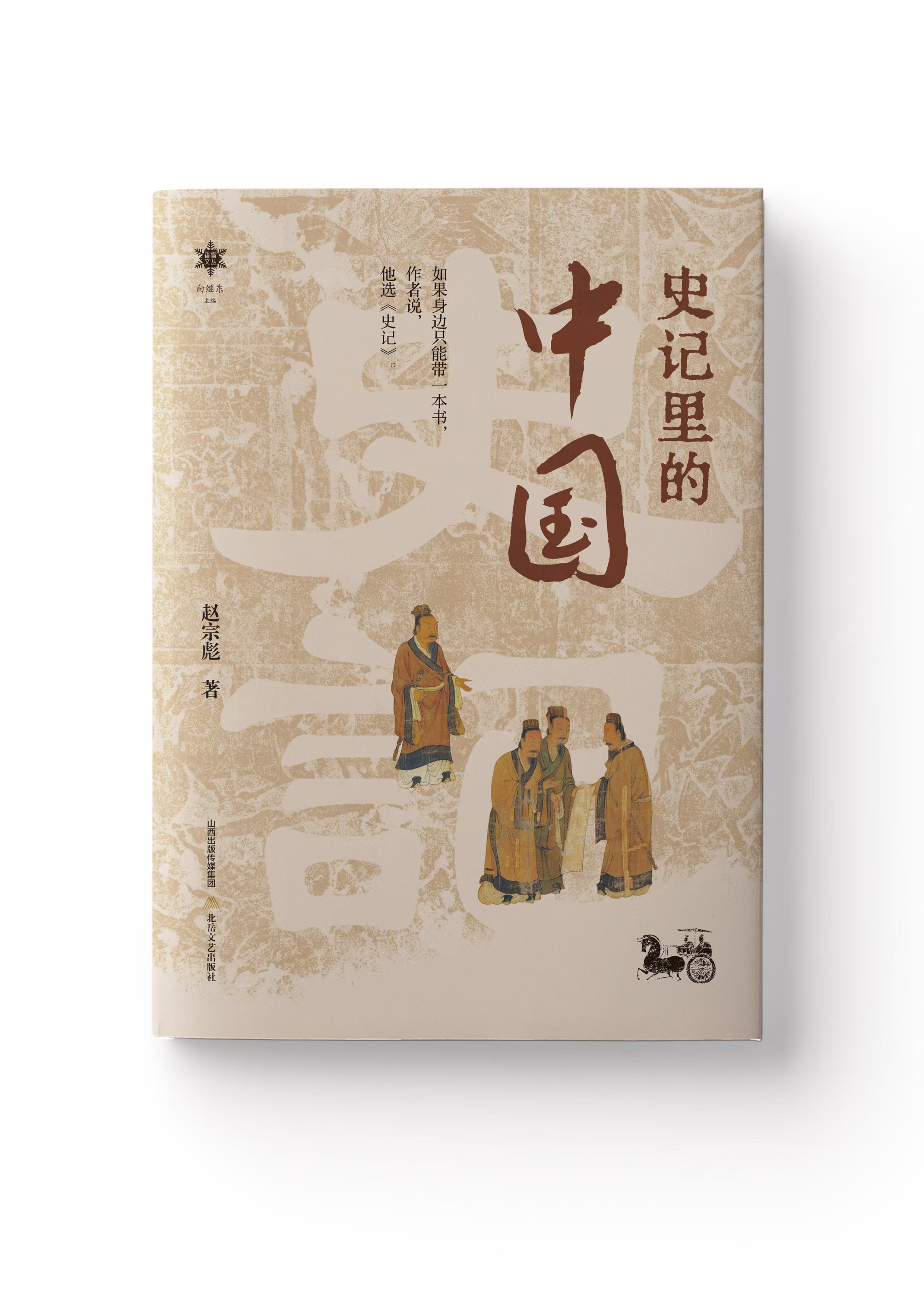
《史记里的中国》书封
乍一看,书名很宏大,写史记、写中国,大约是皇皇巨著。其实,这只是本巴掌大的小书,里头的一篇篇杂文,也短小精悍。
在空中飞行的6个小时,我着迷一般,将书从头到尾读完,灵魂也如同在云端飞翔。合上书,不禁感叹,书本虽小,字里行间,却负载了思想之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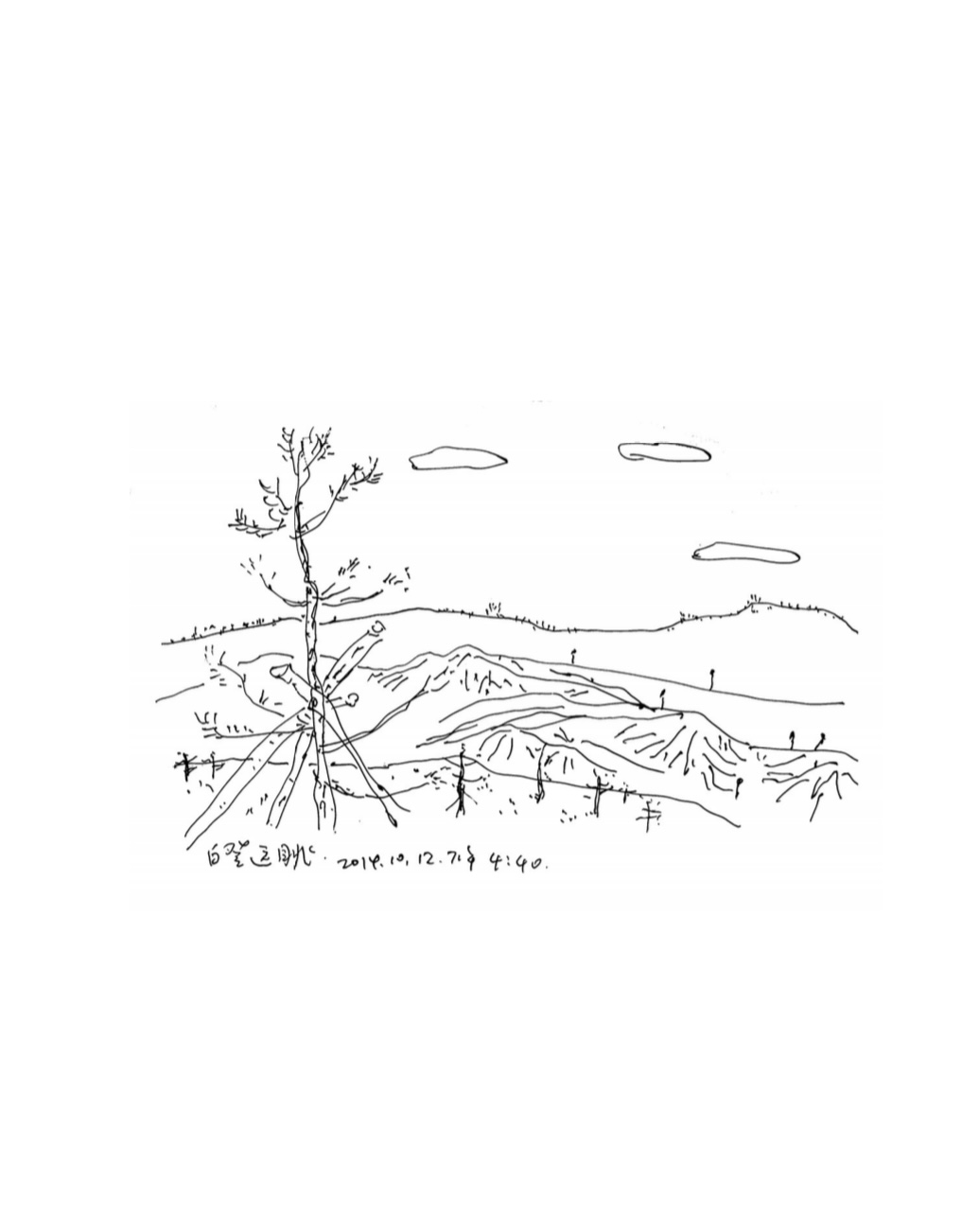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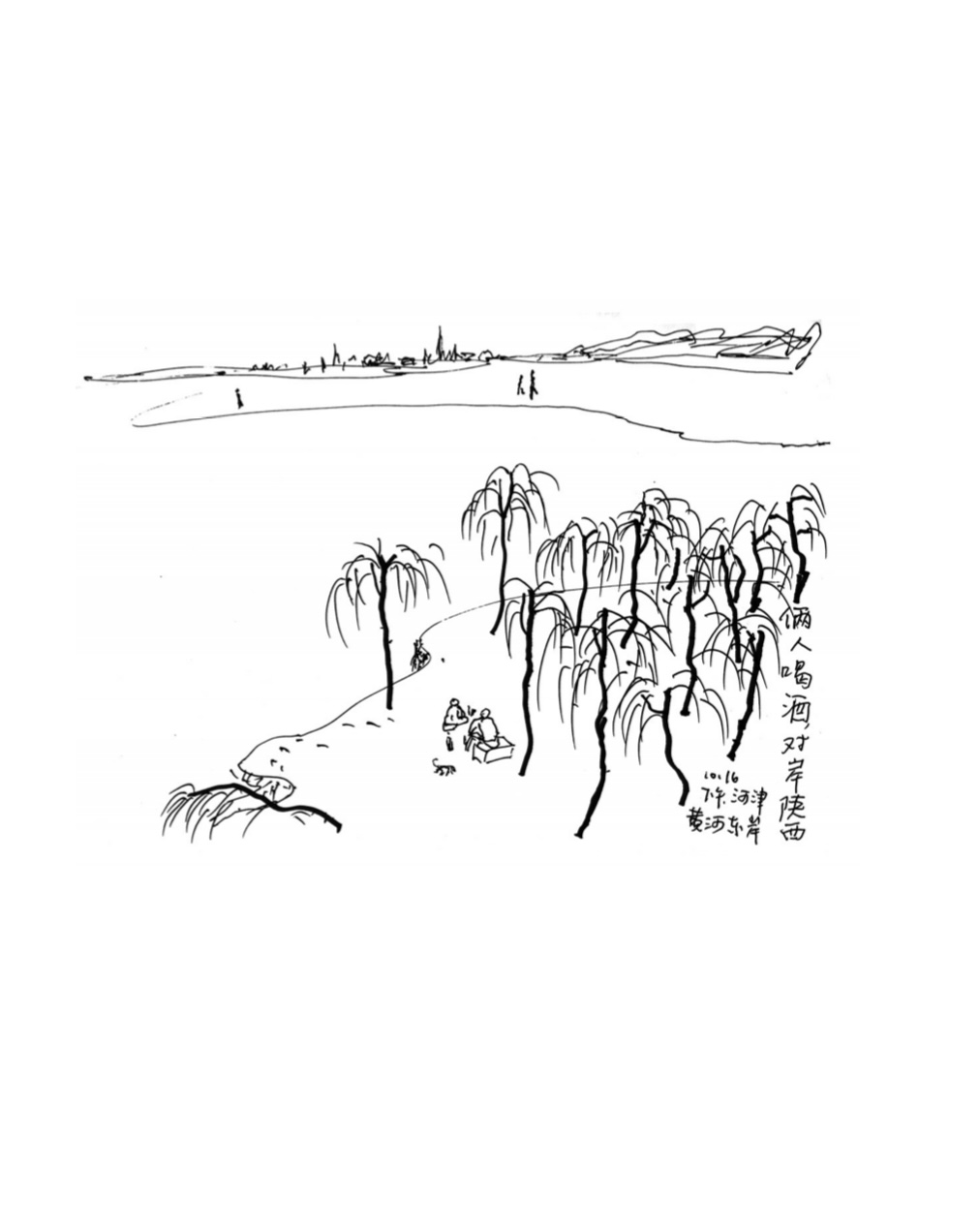
《史记里的中国》插图
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司马迁其人其书的了解,来自语文课本,赵宗彪也不例外。40多年前,他还是个中学生时,读《陈涉世家》,便被其汪洋恣肆的文字所吸引;考入大学后,在校图书馆找到王伯祥编的《史记选》来读,“喜欢得不得了”。
往后,他几将《史记》当作“人生之书”,从少年读到了中年,依然常读常新。他笑称自己是“太史公门下走狗”,并以此为荣。我想,《史记》在经年累月中,也锻造了他的人格——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,这才有了我们熟悉而尊敬的赵宗彪先生。
《史记》所描述的中国,正值中华文明的青春期。这时候的人们,心情开朗、体格刚健,尤其跃动着足以让人类自豪的人的精神。书中无论是帝王、士人,还是贩夫走卒,都有着不可屈服的尊严和斗志。赵宗彪在《史记里的中国》里写道:“《史记》最让人激动的,永远是人,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,有着高贵的心灵、不屈的精神、充沛的豪情。”
赵宗彪读《史记》,读的是“尊严”二字。我尤其喜欢书中《个人的战争》一篇,说的是“羊斟惭羹”的故事。
公元前607年,郑、宋两国交战。战前,宋国主将华元为了鼓舞士气,杀羊犒劳将士。羊肉本应人人有份,华元却没有把肉分给他的车夫羊斟,甚至连一碗羊汤都没分给他。战争开打后,羊斟径直把战车开到了敌军阵中,华元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郑国士兵活捉了。羊斟得意地说:“分羊肉的事情,你说了算;驾驭战车的事情,我说了算!”
羊斟这件事,历来被看作是以私害公的典型,《左传》称羊斟是个“无良”之人,极为鄙视。赵宗彪却不这么看,他说,作为一个社会成员,身份地位千差万别;但作为一个人,尊严是一样的。羊斟受到不公正待遇,他当然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抗争。这是他“个人的战争”,也是小人物对抗特权的战争。
最终,羊斟赢了。这个小人物留给历史一个铿锵之声:任何人的尊严,彼此并无区别。强者也别太得意,强弱之间,有时转换是很容易的。
赵宗彪读《史记》,读的是“文明”二字。什么是文明?他在《敢于失败的英雄》一文中写道:“心中有自律的底线、行动有严格的规矩,他们可以不计成败得失,自觉地坚守心中的底线和规矩,并以此为荣。”
春秋到战国的四五百年,旷日持久的战争,使得中国的兵法异常发达。孙子兵法、吴子兵法,这个法那个法,说到底就是两个字:骗人。而像遵守“礼义之兵”的宋襄公,则被当成了傻子。
所以到后来,斩草除根、屠城活埋、杀人盈城、杀人盈野,成为了战争的常态。野蛮能战胜文明,也就不稀奇了。
赵宗彪认为,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,“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时空,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,而是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”。对宋襄公,司马迁无疑采取了褒奖的态度:“襄公既败于泓,而君子或以为多,伤中国阙礼义,褒之也,宋襄之有礼让也。”(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)。
司马迁为中国历史留下一把尺子,用作度量文明的标准——什么样的社会,才是文明的社会;什么样的人,才是值得敬佩的人。秦汉以后的两千年,中国人尊崇那些失败的英雄,诸葛亮、岳飞、文天祥、于谦等,无不经得起太史公之尺的衡量。
当下这个时代,追随司马迁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赵宗彪则通过一本小书,重新捡起了司马迁的尺子,告诉我们,对于面向世界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,这把尺子依然适用。
(作者吴世渊,系《台州日报》记者、副刊编辑,浙江省作协会员)

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”新媒体矩阵:













集团旗下品牌新媒体矩阵:





